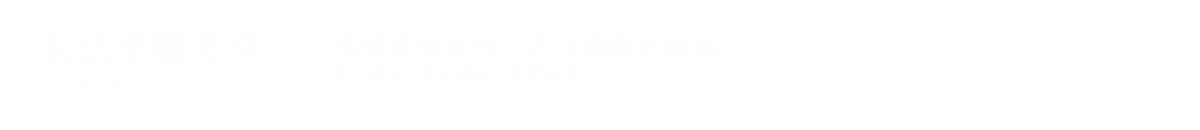业务随笔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及追偿权问题研究
张毅 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英国法学家霍布斯曾言,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作为法律基础性价值之一的安全,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补充责任,作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产生的一种特殊民事责任,系指在两个针对同一权利主体和同一损害的具有主次关系或主次之分的民事责任中,对主责任起着补充作用且法律效力低于主责任的责任,是次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牵连性责任。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必须有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在补充责任中,损害的事实是由主责任人的直接行为造成的。
(二)同一损害事实中存在着两个关联性的法律事实。主要责任人的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补充责任人的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重要条件,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两种相关联系的法律关系。
(三)补充责任必须同主责任相对应。补充责任是一种牵连性责任,若没有主责任,补充责任便缺少存在的前提。
(四)补充责任是经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而产生。补充责任的创设与适用的受到严格的限制,即避免补充责任的肆意滥用,好相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分布在第34条第2款[1]、第37条第2款[2]、第40条[3],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对劳务派遣中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时未尽选任义务的补充责任、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第三人侵权时未尽安全好义务的补充责任以及教育机构对无限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第三人人身损害时未尽管理职责的补充责任。
本文主要讨论此三类特殊侵权中补充责任的责任承担及追偿权问题。补充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牵连性责任,是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或虽确定但无资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补充责任人在其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即存在责任承担的先后顺序与责任范围的大小的不同。对于补充责任的责任承担及追偿权问题,我们可以从下述方面进行理解:
(一)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不构成共同侵权。所谓共同侵权,包括因共同加害行为导致的共同侵权与共同危险行为导致的共同侵权,即二人以上基于意思联络共同实施加害行为或二人以上虽无意思联络但同时实施了数个均有可能造成同一损害结果且无法确定实际责任人而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在《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37条、第40条规定的情形中,补充责任人主观上虽有不同内容的过错,但与直接责任人没有任何形式的意思联络,客观上直接责任人的积极的作为行为与补充责任人的消较的不作为行为亦非直接结合对被侵权人造成同一损害结果,即补充责任人的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虽具有相当的关联性,但其并非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仅因原因力上的贡献而应被科责。所以,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不构成共同侵权,二者亦不能承担对外共同、对内按份的连带责任,而是基于“责任自负原则”承担各自的直接责任,进而缺乏行使追偿权的正当权源。
(二)补充责任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及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因果关系可以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前者成立的条件是,补充责任人违反不同形式的作为义务的过错。但后者范围的确定并不取决于其过错,而取决于其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补充责任人仅承担其能够有效防止或制止损害结果发生范围内的责任,进而体现行为的可责性与责任范围的相适应性之间的均衡。
(三)补充责任人不得以其承担补充责任为由向直接责任人行使追偿权。《最高法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在先)与《侵权责任法》(2009,在后)关于追偿权的规定,总体上呈现出由“肯定说”到“否定说”的渐进式的变化。基于“责任自负原则”的考虑,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并无追偿权,因为对补充责任人疏于作为义务的过错以及其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的相当因果关系的可责性即体现在其承担补充责任本身。此时,补充责任对于补充责任人而言就是较终责任,不得向直接责任人追偿。
到此,我们基本可以回答《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40条关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第三人侵权时未尽安全好义务的补充责任、教育机构对无限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第三人人身损害时未尽管理职责的补充责任以及相关追偿权的问题。
需要重点且详细阐述的是《侵权责任法》第34条关于劳务派遣单位对劳务派遣中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时未尽选任义务的补充责任及其追偿权的问题。根据前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劳务派遣中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用工单位基于其对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人格的吸收,对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未尽选任责任的,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即在用工单位无法确定或无资力承担责任时,承担其责任范围内的补充责任且不得向用人单位追偿。但在此法律关系中,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可以向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的问题,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在侵权责任法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用人单位是否享有对工作人员的追偿权”问题的说明,体现出立法者倾向于肯定用人单位享有追偿权。究其原因,在于只要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在其经营范围或授权范围内的一切行为,从第三人视角即外观上看来,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的人格已经为用人单位法律拟制的独立人格所吸收,其独立性不复存在,其不再享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进而其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思,无论是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合法行为或侵权行为,逻辑上均为用人单位的行为,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责任。若用人单位能够举证侵权行为系因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且该行为超过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的,用人单位可以向工作人员进行追偿。但是,在劳务派遣中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情况下,用工单位有权在特定情形下向工作人员进行追偿,已无需赘述。至于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可向工作人员进行追偿的问题,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实际控制指挥是各种用工形式中的稳定因素和共同的核心内容,也是判断侵权责任承担者的主要依据。劳务派遣单位将劳动者派至用工单位后,不再对劳动者的具体活动进行指挥监督,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指挥监督下从事劳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正是实际指挥控制与监督的关系。此时,劳务派遣人员的同一人格不可能同时被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的独立人格所同时吸收。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人员的责任划分,是基于其人格上的全部或部分重合。此时,劳务派遣单位便不再享受对劳务派遣人员的追偿权,即便工作人员是一切风险、危害或损害的实际创造者。